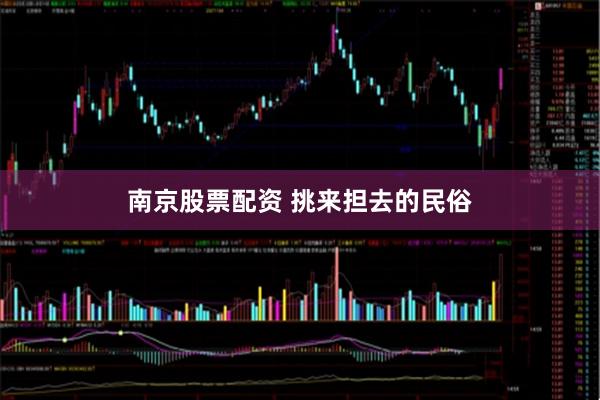
炎热的夏日到来,包子开始在眼前晃悠,扁担上的民俗,一年一度的,又将到来。
皖南歙东深山,农历的六月,是很有盼头的。夏茶,绿中透红,已摘完了;玉米、山芋的头遍草,也锄好了。村民突然就空闲下来,干点什么好呢?民以食为天,慰藉一下春来夏至的劳累,顺带走走亲戚。相邻的几个村庄,陆续开始过流传数百年的节日,走村吃包子。
徽州多山,层峦叠嶂,山峦间或是山脚下,都是族聚居住的村落。一个村一个大姓,一个村一个节日。你在山这边,我在山那边;你在山顶上,我在大河畔。先人带着兄弟、儿子迁徙,择地而居,依山傍水,砍树搭棚,开荒种地,开枝散叶,慢慢繁衍生息,陆续成为千余人的村庄。同姓不婚,相邻几个村,你嫁过去,我娶过来,村子之间从泥土路变成了青石板,来来往往,热闹非凡。
日子闲下来,弄点吃吃,邀三五朋友,走走亲戚,半年没见了,小聚需要理由,也不需多言,是谁定的过阴历日子,我不知道。等我懂事时,只知道到大谷运过六月一,绩溪县上庄、大源有六月六,汪满田是六月十,桃坑是六月半,桃岭是七月半。什么时候约定排序的,问了村里的老人,他们也只是呵呵一笑:拿来了,你只管吃就是,那么大的包子都堵不住你的嘴啊。这些村,以我家为圆心,或溯溪而上,或是翻山越岭,近者五里路,远者十余里,他们都要做包子的。
端午节前,嫁到汪满田的小姨来看外公,都过来打招呼:“六月十,记着到汪满田去吃包子。”我看了看父母,他们总是笑笑:“作业做完,地里草拔好,你就去……”离过节还远,玉米才几寸高,还是刚站稳脚跟。我心里着急忙慌:哎哟,还不发暑假作业呢!玉米地里的草,赶紧长出来,早点拔掉。
日子在望眼欲穿中到来,唉,学校还在上课,不是星期天,去不了。中午到家的时候,厨房菜篮里满满的,是芝麻糖包和豆腐笋干包,还有白色的圆圆米糕,用高粱煮出的红汁点上去的红痣,看着就是一份美好。
黄芝麻黑芝麻,炒熟舂碎拌上白糖。这芝麻糖馅的包子,圆鼓鼓的,就简单几个褶。豆腐笋干馅的包子,是半月形的,褶皱就清晰许多。这对好久没吃过的我来说,妥妥的美食。豆腐笋干的要先吃,不然天气热要坏了;芝麻糖的,不着急。接连几天,厨房的蒸笼上,都是包子,好吃的包子啊!
六月的节庆一个人是忙不过来的,女主人早就打过了招呼,娘家的嫂子、弟媳,外村的姐妹,“呼啦”一下,提前一天就来了。哥嫂姐妹们难得一聚,厨房里热热闹闹。“嘭嘭嘭”的声音,自家家户户传出,从午夜开始响起。厨房大锅上的蒸笼,一直冒烟到天明。
做包子的辛苦,挑包子送的也辛苦。我还没去学校,小姨夫满脸大汗拎着包子进门:快快快,找个菜篮来装。我诧异着,这么早。他说,好几个村哦,还有桃坑西坑,竦坑最远,老丈人家先送,不早点来不及,到下午馊掉就不能送亲眷咯。谁家没有几个外村的亲戚呢,芝麻糖的几个、豆腐笋干的几个,米糕几个,看似不多,一放进菜篮,就满了。几家亲戚,就得准备几份。没有公路,只有山路,一担大茶篮满当当地装满了包子和米糕,盖着几片手掌一样的青绿芦叶。手里还要拎着一菜篮,不然亲戚不够分。
可怜的小姨夫,年年挑一大担包子来竦坑,每个亲戚都要挑送。我忍不住说,小姨夫家都要挑空。母亲笑了,又吃不穷的。他家挑过来,你家挑过去的,不还是在自家锅里。你是没看到他来竦坑过十月半,这家一串粽子,那家一串粽子,到时又是满满的一担挑到汪满田去,有得吃呢。
一年一度的夏季吃包子,秋季吃粽子,挑来担去,山林小道,村庄石板,快快乐乐的,日子很快就过去了。我吃了很多年,回味了很多年。等我出了山,回望老家的包子粽子,这淳朴的来往,成了亲情的维系。六月里小麦丰收了,忙里有闲,做包子;十月稻谷丰收了,秋冬有空,包粽子。你家吃罢我登场,快乐着每个村庄,惬意着每个人。2018年9月,农民有了丰收节,这送来送去的欢乐,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庆丰节。
陆陆续续,我们这代人都进了县城,父辈们都在乡下。六月十、十月半的风俗,依旧年复一年地上演。两个老表回家过节,专门给我带包子来,放在冰箱里,蒸在饭锅上,甜上半个月。我在秋天里回家,拿粽子出来的时候,也联系他们,一家一串,一串十个。
这挑来拎去的风俗南京股票配资,就这样年复一年,代代相传,迎来送往。
优先配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


